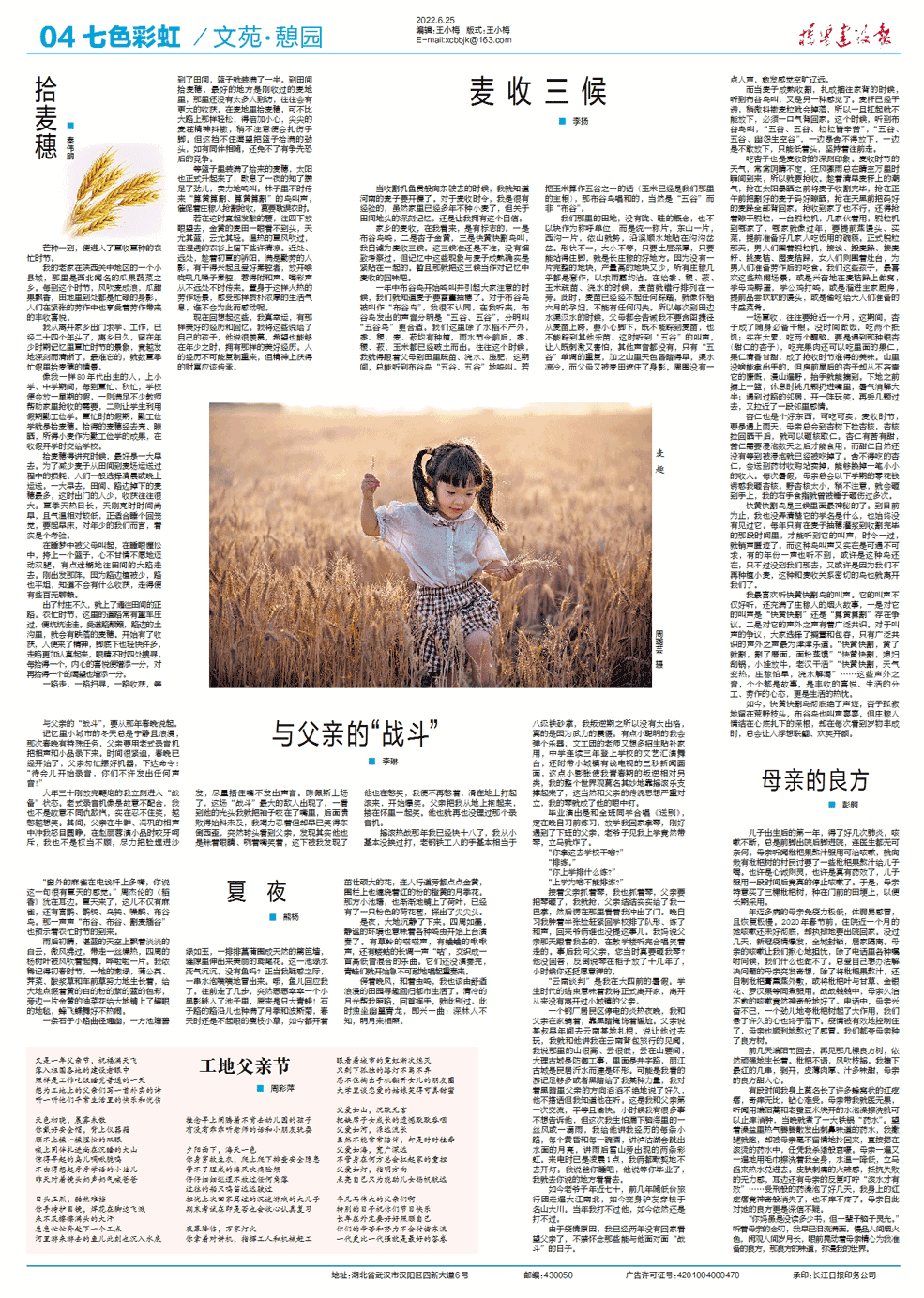与父亲的“战斗”
来源: 作者:李琳
与父亲的“战斗”,要从那年春晚说起。
记忆里小城市的冬天总是宁静且浪漫,那次春晚有特殊任务,父亲要用老式录音机把相声和小品录下来。时间很紧迫,春晚已经开始了,父亲匆忙摆好机器,下达命令:“待会儿开始录音,你们不许发出任何声音!”
大年三十刚放完鞭炮的我立刻进入“战备”状态。老式录音机像是故意不配合,我也不是故意不同仇敌忾,实在忍不住笑,越憋越想笑。其间,父亲在牛群、冯巩的相声中冲我怒目圆睁,在赵丽蓉演小品时咬牙呵斥,我也不是权当不顾,尽力把脸埋进沙发,尽量捂住嘴不发出声音。陈佩斯上场了,这场“战斗”最大的敌人出现了,一看到他的光头我就把袖子咬在了嘴里,后面溃败得始料未及,我竭力忍着但却早已笑得东倒西歪,突然转头看到父亲,发现其实他也是眯着眼睛、咧着嘴笑着,这下被我发现了他也在憋笑,我便不再憋着,滑在地上打起滚来,开始爆笑。父亲把我从地上抱起来,搂在怀里一起笑。他也就再也没理过那个录音机。
摇滚热战那年我已经快十八了,我从小基本没挨过打,老钢铁工人的手基本相当于八级铁砂掌,我叛逆期之所以没有太出格,真的是因为武力的震慑。有点小聪明的我会弹个乐器,文工团的老师又想多招生贴补家用,中学连续三年登上学校的文艺汇演舞台,还附带小城镇有线电视的三秒新闻画面,这点小膨胀使我青春期的叛逆相对另类,我的整个世界观莫名其妙地靠摇滚乐支撑起来了,这当然和父亲的传统思想严重对立,我的琴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
毕业演出是和全班同学合唱《送别》,定在晚自习前练习,放学我回家拿琴,刚好遇到了下班的父亲。老爷子见我上学竟然带琴,立马就炸了。
“你拿这去学校干啥?”
“排练。”
“你上学排什么练?”
“上学为啥不能排练?”
接着父亲抓着琴,我也抓着琴,父亲要把琴砸了,我就抢,父亲结结实实给了我一巴掌,然后愣在那里看着我冲出了门。晚自习我肿着半张脸赶紧回学校排了队形、练了和声,回来爷俩谁也没提这事儿。我妈说父亲那天跟着我去的,在教学楼听完合唱笑着走的。事后我问父亲,您当时真要砸我琴?他没回答,反倒说琴在柜子放了十几年了,小时候你还挺愿意弹的。
“云南谈判”是我在大四前的暑假。学生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我将正式离开家,离开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城镇的父亲。
一个钢厂居民区停电的炎热夜晚,我和父亲在家躺着,靠黑暗掩饰着尴尬。父亲说某叔早年间去云南某地扎根,说让他过去玩,我就和他讲我在云南背包旅行的见闻,我说那里的山很高、云很低,云在山腰间,大理古城是防御工事,里面是井字路,丽江古城是民居沂水而建是环形。可能是我看的游记足够多或者黑暗给了我某种力量,我对着黑暗里父亲的方向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久,他不搭话但我知道他在听。这是我和父亲第一次交流,平等且愉快。小时候我有很多事不想告诉他,但这次我生怕漏下脑海里的一丝风或一滴雨,我给他讲我经历的每条小路,每个黄昏和每一碗酒,讲泸沽湖会跳出水面的月亮,讲雨后雪山旁出现的两条彩虹。来电时已是凌晨1点,我俩都默契地不去开灯。我说爸你睡吧,他说等你毕业了,我就去你说的地方看看去。
如今老爷子年近七十,前几年随低价旅行团走遍大江南北,如今变身驴友穿梭于名山大川。当年我打不过他,如今依然还是打不过。
由于疫情原因,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看望父亲了,不禁怀念那些能与他面对面“战斗”的日子。